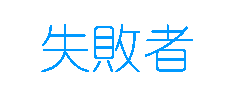社會性死亡
嚴歌苓一夜之間在「簡體中文互聯網」被社會性死亡了,這是可以預見的,頗令人唏噓。我也翻出了另一則當時在未註銷豆瓣之前曾發表於豆瓣的文章,不過因為那個時候豆瓣的審查機製,這篇文章只有前半部分。
《我也曾幻想過社會性自殺》(原文已刪)
找了很多數據,始終沒有找到最新的。
最終只能找到18年前的數據:2001年日本警方正式受理的、要求幫助尋找離家出走者案例已高達10萬2130起。自1984年以來,一年中的離家出走者時隔17年再次超過了10萬人。與以往相比,兒童、學生、無業人員以及公司職員等在離家出走者中所占的比例明顯增加。
然而這個數值還在以恐怖的速度增加著。出門扔個垃圾就再也沒有回來的劇情,我們只是在日劇中看到過。然而事實上,這樣的劇情隔三差五就會發生幾起。有時候我也在想,如果有一天,我拎著個口袋,沒有帶任何可以證明自己的證件和通信工具,我頓生離開的心思,我能去哪里,又想要過怎樣的生活?
另一種更為巧妙的「失蹤」,不只是離家出走這麽簡單。一些在重大事故中活下來的幸存者,會利用失蹤的身份,去了另一個城市開始了被冠於另一個身份的生活。
我曾羨慕過這樣的方式,還以此作為故事背景,寫過《新生協議》的故事。但是這樣的劇情終究只是規則中一個不起眼的bug,而這個bug在社會的進程之中早早地被修復。如果可以,我倒想做一筆這樣的生意,利用事故,讓人們失蹤,然後開始一段全新的生活。
無論是突然的離家出走,或是利用事故失蹤掉自己的身份,我把它稱為「社會性自殺」,肉體還活著,但是身份已經成為了被寫在失蹤證明或是被刻在墓碑上的文字了。
前幾天,看到一位豆瓣友鄰的簽名——我曾想過自己活不過26歲。
我也有過這樣的想法,我或許會在35歲突然選擇自殺——或許是中二病,也或許只是自己的無心之談。真的到了30歲的時候,卻又想著,如果自己真的能活到35歲,那個時候,自己又將有怎樣的想法,又顛覆了自己人生多少次,這樣也未嘗不是件有趣的事情。
大概是4年前吧,也是這個時候,我開始計劃自殺,計劃的細節已經到了購買怎樣的麻繩,然後要尋找到一顆怎樣的石頭,才能讓我沈入家門口不遠的江中。
有人說,自殺的想法就是傷疤,供人一次次地揭開尋求別人的同情。這句話只對一半,因為我並沒有打算一次次揭開,是因為我早就忘記這個傷疤在什麽地方了。
你活下來了,就必須要面對比死亡更復雜的事情,他們在你身上留下了只會讓你更加堅強的傷疤——死並不可怕,等死才是這個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有些傷疤,如果不是你總記得在哪里,又怎麽會想要一次次地揭開它?
你想離開嗎?如果你真的想離開,又怎麽可能回去思考離開之後的問題?
社會性自殺,這是一個悖論,你要告別你自己的身份,但是你又必須帶著原本身份所擁有的東西繼續活著——對一個人的愛、對一個人的恨、身體里的病毒、肌體里的癌變、包括我在《新生協議》里提到的「可是我還是喜歡牛奶配上草莓醬」。
當一天,我的腦子突然回憶起「扔垃圾離家出走」的橋段,我在那個時候問了自己一個問題——我回不了家門嗎?是我不想回去,還是我已經回不去了?這兩者的結果看上去一樣,但是卻各有各的悲劇。
前者,你會不會有一天,突然又想回去了?
後者,你會帶著回不去的痛苦,去用一輩子的時間,尋找一個可以回去的地方。
哪一種更痛苦,我想是第一種吧。我告別了所有的一切開始一段新的生活,卻在某一天,我意識到我依舊記得那天離開時,穿著怎樣的衣服,恨著怎樣的人……
逃走吧,在你還能找回家的地方停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