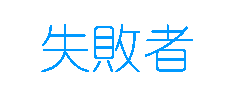我都破防了你為什麽不能破防
不知道從什麽時候開始,「破防」這個詞就鋪天蓋地地爛開了,大概是因為官媒也開始用這些流行語,所以畫風就變得惡心起來。官媒往往對一個網絡用語加以使用時,一定會先采用「重新定義」的方式,摒棄掉該詞組原來可能涵蓋的「負能量」,然後重新註入仿佛人們聽到這個詞就可以渾身充滿幹勁再長一寸多長多割的「正能量」。這種無形地拉踩和對前續定義的否定的方式,是官媒拿走一個網絡用於慣用的手段,如今已經見怪不怪,你可能覺得他創造不出什麽新意,但至少他有能力讓原本的網絡笑點都成了春節晚會本身的笑話。
「破防」大概也是一個被官媒重新定義,而變得惡臭的詞組之一。
細數一下最近有什麽是值得我「破防」的事情,沒有找到不說,我反而還開始重新懷疑起自己——是不是我越來越冷血了,為什麽明明有些值得同情、值得傷感、值得跟著網絡一起感動、值得跟著不滿之聲生氣的事情,我都毫無反應。最近有一個癌癥病人家屬,在醫院門口下跪祈求醫院接收病人的視頻,讓很多人「破防」,為醫療體系的冷漠感到痛恨,對失去丈夫的女人感到可憐,我努過力了,最後只能為自己的「冷血」感到遺憾,而且我竟然還評價了一句:「還好我是去年被120送進醫院的。」
倒不是說自己的「防」夠高了,而是「破」事兒太多了,「防」與「不防」都已經無所謂了,見怪不怪,但又必須隨時保持一份謙卑和敬畏——因為這些「破」事兒,也很有可能在未來什麽時候發生到自己身上,而那個時候「破防」的就真的是自己了。大不了,上網發微博訴苦,在微信朋友圈控訴,還得保持一份清醒:在外國媒體要采訪我的時候做出義正言辭的拒絕,不然那時候明明想讓大家跟著「破防」的事,倒變成了發給外網「遞刀子」的鬧劇了。
我記得小時候,還允許私搭靈堂那會,一般有人去世後,都會由逝者家屬聘用一家附近的喪事一條龍,在家屬院、小區內的空地里,用彩條布在空地上臨時搭建出一個靈堂,靈堂的數量是有暗自比較之說法的,搭一個的往往是普通家庭,而搭兩個的、三個的,甚至是好幾個前後穿成一條直線的,不僅闊氣,還是一種對死者的尊重。靈堂一般要停喪三天三夜,第四天一早天蒙蒙亮的時候,才將死者送去火葬場做最後一道流程(初稿的時候這里寫的是「工藝」,媽的)。因為靈堂搭在家屬院、小區的內部或是附近路邊,難免會阻擋別人進進出出的行道,這多少有點「不吉利」,所以這些靈堂並不只有停喪這一個功能,為了打消別人「不吉利」的顧慮和對別人打擾的愧疚,靈堂則成了一個這個家屬院的臨時娛樂場所,以「鬧喪」的方式讓喪事變得沒有那麽的悲慘。
在這三天三夜的期間,往往前兩天是留給親屬的,披麻戴孝的親人按照輩分跪在棺材前磕頭祭拜,從異地趕回的親屬,也盡量要在第二天內完成吊唁,那時候整個靈堂的彩棚鋼架上,都會掛滿前來吊唁的親友、鄰居送來的棉被。至今我都沒有搞懂,為什麽那個時候需要送棉被,大概是給那些床榻少一人的失去至親之人一些「溫暖」罷。從第一天晚上開始,靈堂就變成了附近鄰居的娛樂場所,熱茶糖果、花生瓜子、三餐宵夜都是無限量供應,參加喪事(俗稱守夜)的親友鄰居,會打通宵麻將、撲克等等。熱鬧大概是對死者的一種尊重,避免他們在前往鬼門關報道前的這幾天感到「孤獨」。也有一種說法,足夠熱鬧的場景,是想讓去世的人能夠徹底放心地離開。第三天晚上往往是最熱鬧的,因為「鬧喪」的習俗,很多有錢的家庭都會請來專業的喪事一條龍出隊。第三天晚上的表演安排一般被我稱之為「匯報演出」(重慶話:死人子板板表演),匯報演出匯報的是母慈兒孝妻順嗣從,就算在分崩離析的家庭,鬥爭得厲害的妯娌連襟伯仲叔季,再不對付的婆媳丈婿兄弟姐妹,都必須在今晚成為這個世界上最孝順最聽話最和睦的一家人,以完成死者希望看到大家庭和睦的遺願。
「匯報演出」一般都是以「呼喚」開始,若去世的是父親,那一定是以《不老的爸爸》暖場開嗓,若去世的是母親,則以《燭光里的媽媽》開場,至今我都能隨口哼唱這兩首歌,大概就是因為小時候見過太多「匯報演出」。現在想想啊,開場曲其實並不平等,為什麽去世的是父親,得在這麽歡快的曲目中開始?而失去母親的,第一首歌就要直擊心靈、破防家人們。一般來說,第一首歌唱的是什麽,就能斷定這個家庭逝去的是誰。這個時候一定有人提問了,如果逝去的不是父母親呢?那一般開場都是一些不搭邊的抒情音樂,當然也有膽子大的敢以《故鄉的雲》來作為開嗓曲,現在想想也是一個敢唱一個敢聽。
「匯報演出」的升華往往是在壓軸部分,這個時候一般會是一個中氣十足的主持人(一般主持人和歌者是同一個人)在臺上聲淚俱下地獨白,在準備演出短暫的時間內,他居然能記住關於死者的相關信息脫稿演講,然後在上面哭訴他的離開對他的不舍對他的緬懷。雖然我不知道這里面的奧秘,但我覺得他哭得越慘他拿到的紅包越多。他的哭聲幾乎可以將整個「匯報演出」沖到高潮,在幾百米的範圍以內,都能聽到他呼天搶地的痛哭聲。壓軸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把現場所有人的頻道都調整到對死者的緬懷,他們停下了手中端起的茶杯,吐出了嘴里的瓜子殼,家人們拿起了紙巾準備擦淚,搓麻的人也顧不上這一局還做不做清一色,鬥地主的耍千從牌堆里抽出幾張牌給自己做了兩個三帶一都不會被人發現——這些久經沙場的、什麽靈堂、什麽家庭、什麽人際矛盾都見過的喪事一條龍,就有能力能讓在場的所有人都在那個時候痛哭流涕,仿佛那些原本存在於家庭之中的糾紛與矛盾都(在當下)被化開了。壓軸之後,主持人會給大家一些緩沖的時間,等時機一到,便開始了壓臺演出,壓臺演出一般是歡快的音樂,頗有中國曲藝里「起承轉合」的精髓,從「鬧」到「哭」,最後再回到「鬧」。一般來說,壓臺音樂都會選曲《明天會更好》這一類的音樂,預示對未來美好的期盼,就算死者已逝,但是活著的人生活還是得繼續的。不過我也見過離譜的,選曲《快樂老家》:「跟我走吧,天亮就出發」,別說,時間還對得上。
火化之前還有最後一場熱鬧的表演,第四天早上,趁太陽還沒有出來之前,死者會被送往火葬場,而在送往火葬場的途中,會由一個小皮卡運輸棺材,在棺材周圍同時還有樂隊演奏著哀樂,一路撒紙錢一路駛向火葬場,寄托著每個人美好的心願,也駛向了看似美好的遠方。這應該是最後的演出,演出的樂隊往往采用的都是最簡單的樂器,嗩吶、圓號等等,我還見過有薩克斯的,但這種花銷不是一般普通家庭所能承擔的。總之,最後一場演出多有些淒涼,在清晨的公路上,還沒有來得及吃早飯的演奏家們,因為不是飽吹餓唱,演奏出來的聲音也顯得更加的淒涼。哀樂由遠及近,然後又飄向遠方,音樂在這個過程中變調失真,頗有一種火化時熱浪卷散的意味。在太陽升起的那一刻,整個城市歸於正常,只有被過往車輛吹卷到路邊的黃紙錢,還證明著這里有一個生命曾離開,但是太陽照常升起。
你他媽讓我怎麽「破防」?我從小時候開始,就算到了現在,看到的全他媽是喪事喜辦。